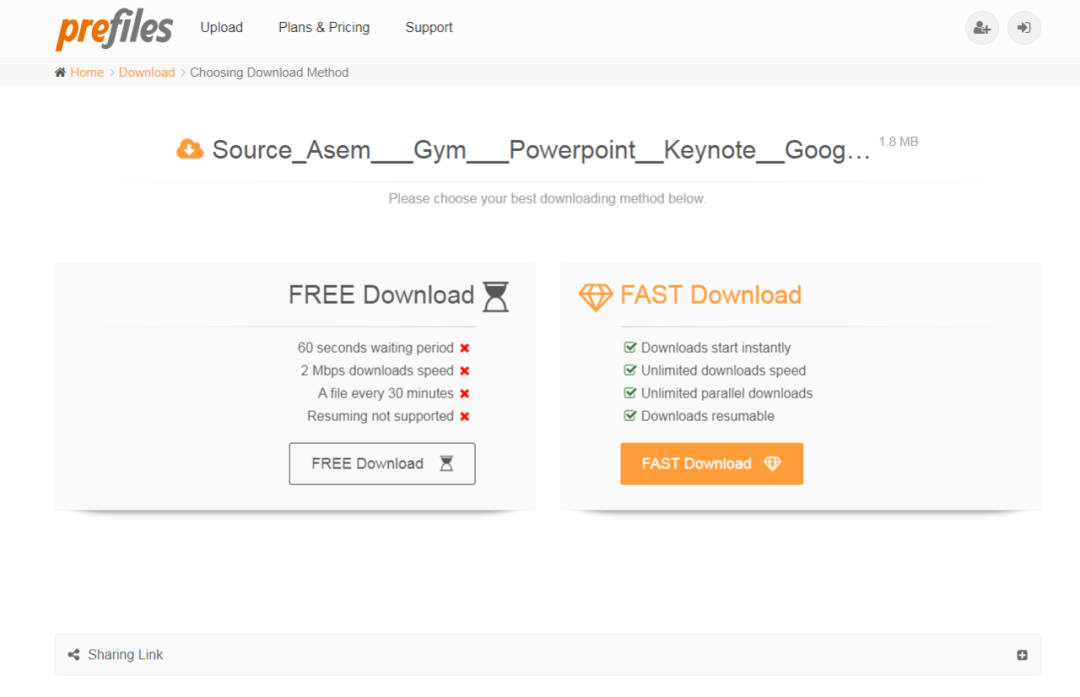报复
我幼时体弱。母亲说我刚出生就营养不良,加上我是家中的老大,父母没有育儿经验,不知道怎么安抚我的肠胃。我断奶时,父亲在邻居建议下买了炼乳,据说我喜欢吃,但一吃就闹肚子,发高烧。节俭的父母大人一边带我看医生,灌小儿土霉素,一边坚持把一瓶炼乳喂我吃完。后来,我基本上是吃粥长大的。心理学教授陈立老师说,在婴儿口腔期,没有得到胃口满足的人,长大都比较馋,甚至容易堕落成美食家,这是一种报复。说起睚眦必报这种事情,还是我们天蝎座干起来更专业。长大后我确实馋的出奇,而且经常深夜发吃,报复社会。

不过很庆幸,我更喜欢粗茶淡饭,美食家什么的,离我依然遥远。
教书匠
我父母都是教师,在烹饪方面没有任何天赋,也没有热情。所以,我对食物有兴趣,没有任何家传的基因。从有记忆开始,我总是觉得邻居家做饭香。有一年,还是初中时代吧,大伯母来我家。课间休息,因为饿,回家找吃的(我家就住在校园里),大伯母用很短的时间,馏了一只馒头,又用酱油和葱花,汆了一碗蛋花汤。这让我起了“比较心”,知道这个世界上,对待吃饭这件事,其实可以更认真的。

老师做的饭不好吃 但还是要热爱老师
第一次下饭馆
除了和父母在旅途中吃过的东西,我第一次吃外面的食物,是在县城里唯一一家饭馆。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学,工作子(抱歉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学名),家里给零花钱,于是带着我去街上。县城中心那家叫胜利饭店的小铺子,国营的,有没有菜我甚至都不记得了,主食有三种:缸贴子、油旋子、火食。缸帖子就是发面烧饼,油旋子是面糊油炸而成的,火食就是今天的油酥烧饼,用油和面,通体焦酥。我吃了一个油旋子,他又掰了一片火食给我,我吃了以后头晕得走不动道儿,坐在文化馆前面的台阶上歇了好长时间,耳边都是工作子取笑的声音。当然这种情况可以解释成,我的肠胃素净惯了,根本不配分解油水。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碳水化合物+动物油脂,就能够迅速给人带来愉悦感这件事情,有所怀疑。甚至后面我的纪录片旁白写作过程中,一遇到类似食物组合,我耳边都能浮现工作子的笑声。
鄙视链
小时候的很多食物,都是自己动手。鱼、青蛙(青蛙是益虫、青蛙是益虫、青蛙是益虫,但那时不懂)、螃蟹、知了幼虫……都是自己捉。有一年外公到我家小住,他把一根自行车的辐条打磨了一下,带我去学校的试验田里捉了一桶黄鳝。那天我家就吃黄鳝,野生的哦。过两天,他又钓了一只老鳖,只用了一根线、一根直的大头针和几块碎的猪肝。回来外公就在院子里杀王八,用一根草秸逗它,拉出脑袋一刀下去……邻居走来串去,很受惊吓,我听见一位长辈颇有微词,说:“他家猪肉都吃不起,净吃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我童年的肉食鄙视链里,猪肉无疑处在顶端。但不知什么时候,人们的看法颠倒了过来。

童年吃的大闸蟹,5毛钱可以买四只
北京
读大学的时候,到了北京,过上集体生活。标志是和同学一起,第一次吃到了涮羊肉。当时大家是AA制,在北京齿轮厂餐厅,每人看着一盘肉,由于生怕被别人吃去,所以一直不敢松筷子。这直接导致羊肉没有烫熟,尤其是筷子夹着的那一部分。我脆弱的草食的胃,难以承受,拉了三天肚子。不过当时北京物价很低,同学经常一人凑两块钱,就可以去吃王府井的湘蜀餐厅,或是西单的四川饭店小吃部。当时小吃部的价格我至今记得,麻婆豆腐7毛,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9毛,最贵的是荔枝肉片,1块2。王府井和西单当年一直是北京的商业中心,餐厅也比较集中。很多年后,在广西山区拍片,没吃的,剧组几个人躺在床上生聊。我能从宣武门内开始,烤肉宛、玉华台一路向北,聊到砂锅居、西四包子铺……我说着,低矮的蚊帐里,不断传来吞咽的声响。
美食
第一次知道"美食"这个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还在读书的我,作为摄影助理,陪在央视工作的师兄拍片。那个片子叫《首届中国美食节》,全聚德、仿膳、建国饭店……一路拍,一路吃,我吃了中餐,也吃了西餐,开荤了。记得在北展的潮阳舫,好像是这个名字,第一次吃到了鱼翅。上来的时候,灯光师傅说:“我不吃粉丝,替我撤了吧”。冷场了一下,立刻有人取笑他,这是鱼翅,不是粉丝。我也跟着取笑,就像工作子当年取笑我一样,其实,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鱼翅长什么样。我是多么虚荣的一个青年啊。那时候,北京还是一个平民为主体的社会,我对美食最质朴的理解就是,它不是普通人能吃得到的东西。
七把叉
小时候有一本小人书叫《七把叉》,说的是南美洲一个贫困的少年,因为饭量奇大,被电视台选秀参加大胃王比赛,最后撑死了的故事。我很怀疑这个中译本的作者认识我,因为连环画上的七把叉与我形似。从少年到青年,我都以饭量大著称,尽管我的腰围不到二尺,体型像个豆芽菜。平生饭量最大的一次,是参加工作那年,我们在房山乡下“锻炼”。整整一个月都呆在村里,嘴里淡出鸟了。终于接到通知,到窦店镇,在当时的广电部干校集中。一个下午,饿着肚子听窦店的支部书记仉振亮作报告。晚上在食堂会餐,一桌子菜,主食不用饭票随便打。我先去窗口要了三个馒头,每个二两。没感觉啊,只好又了半斤米饭。吃完米饭的时候,喷香的肉饼出来了,于是我吃了半斤肉饼。最后又看有人吃豇豆馅儿的包子,我又吃了六个包子,一两一个。那个晚上,我撑得一宿没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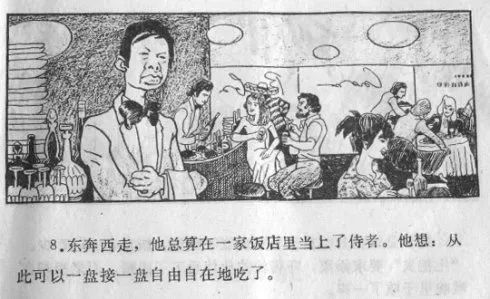
七把叉的漫画
美食雷达
由于从事的职业特殊,经常回不了家,在外头吃饭。我对吃的餐厅和菜,有特殊的记忆天赋,加上又喜欢显摆,不时热情地给别人推荐饭馆。于是在朋友间,渐渐有了“美食雷达”的绰号。但我吃的起的,都是些鸡毛小店,这也算美食?我很疑惑。而且推荐餐厅是一个风险极高的工作,几乎无法积累经验。不是因为餐厅多,而是因为人太复杂——你满怀激情推荐了一堆餐厅,人家不是嫌贵,就是嫌远。我有个朋友叫王三表,有次去上海出差,他让我发餐厅信息给他,我不仅写了各种风味餐厅的地址电话,还写了应该点哪些菜,以及要嘱咐厨师怎么做。当然,如你所知,他最后选择了吉野家。
老男人局
认识王三表是通过吃饭。大概十五年前,我参加了三表他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小宽博客,叫老男人局。除了我之外,他们都是著名网红,都有网名。饭局的局长叫老六,负责组局,他挨着给每人发短信,内容就是一个问号,但总能很快收到十几个感叹号,这是表示当然可以慷慨赴约的意思。老六数学不好,经常订六个人的位子,来二十二个人。老六丝毫不尴尬,现场做调度,让大家围着桌子坐两圈,前后换班吃。其实那时更多的场景,都是大家一起坐着喝酒,跟食物的关联不大。王三表总是带着吉野家的外卖和单反相机前来,全勇先是个素食主义者,杨葵信佛,王小山只空腹喝酒……所以这是一个和美食毫无关联的饭局,吃的是人。我们这些职业完全不同的家伙,一周最多能在一起吃五次。当然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大家为生活所累,见一次面都很困难,老六每每在网上组局,凑三个人都叫大局,六个人就叫超大局了。而更多时候,他都是一缺六。

我看着老六凑一缺六的局(摄影 朱朝晖)
美食专栏
老男人局诞生在博客时代,大家都喜欢吃完写点儿文字挤兑一下同席的人。我被逼无奈,也开始写饭局记事的文字来还嘴,慢慢地不知怎的就成了“美食专栏作家”,在报刊杂志写一些抖机灵的文字。美食圈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所在,和做美食的朋友交往,总能有别样的收获。我对自己的味觉不是特别有信心,尤其是品鉴活动,永远能困扰到我。有一次美食家小宽组织品红酒,摆了二十多瓶在那里。我和几个人站在他对面,先听他普及法国地理知识,罗纳河谷、波尔多、左岸右岸什么的。然后他开了一瓶瓶的酒,跟它们说,醒醒,醒醒——原来垂直品鉴不是把酒垂直倒进嘴里的意思啊?酒倒到杯中,还不能喝,让大家先转着圈儿,叫看酒体。看半天,喝了一口,还不许咽,漱一漱,吐在面前的池子里。这时候宽总背着手小宽博客,让大家谈感受。众说纷纭啊,最后还得他来总结,说出一种味道,还分入口、前味、后味什么的。我是易感体质,他说什么,我口腔里就能脑补出什么,水果、香草、奶酪、坚果,直至托斯卡纳的阳光……慢慢的,对面的身影开始迷离,我感觉宽总就像马戏团的驯兽师,拿着酒瓶做的鞭子,让大家一个挨一个的钻圈。一个多小时,我感受到了做动物的快乐。
美食评价体系
做与食物相关的工作,时间越长,越找不到北。美食有时候很玄妙,有时候也很现实;有时候被时尚掌控,有时候又复辟传统;有时候是情怀,有时候又变成利润。我有很多对美食执着的朋友,比如一个叫散人的老师,蒙着眼睛就能吃出螃蟹是从哪个湖里捞的。这不算玄,还有一个叫老颓的,喝一口茶,就知道泡茶的人前一天晚上约会的姑娘的身高。南宁美食家张发财,每天在南宁寻找一遍做锅包肉最好的饭馆,很偏执。另一个叫一毛的更甚,他选餐厅的标准,一要贵得离奇,二要难吃,这未免太龟毛了。按说一个团队,大家对美食的理解应该大致相同。我有大、小两位同事,小老师是朋友圈特级厨师,每天都能看到她晒各种花枝乱颤的烹饪摆盘,但在工作室厨房却永远见不到她。另一位大老师,重症奶茶爱好者,每天进公司亘古不变手捧一杯楼下的“奈茶的喜”,但选择哪个品种,却完全依据她当天指甲的颜色。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美食的理念都天差地别,怎么让我相信能用一个标准答案来衡量美食呢?所以,前年开始,我不再做任何一个美食评选的评委,因为我不认为有能力代表别人评判食物。
在纪录片里,我们审视所有的食物,往往习惯从四个角度:风土孕育、传统塑造、劳动和智慧、情感和想象力——其实都比较枯燥,这样看到的食物几乎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虽然你们把这些纪录片,统称作“美食纪录片”。
限时特惠:本站持续每日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课程,一年会员仅需要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长微信:Jiuc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