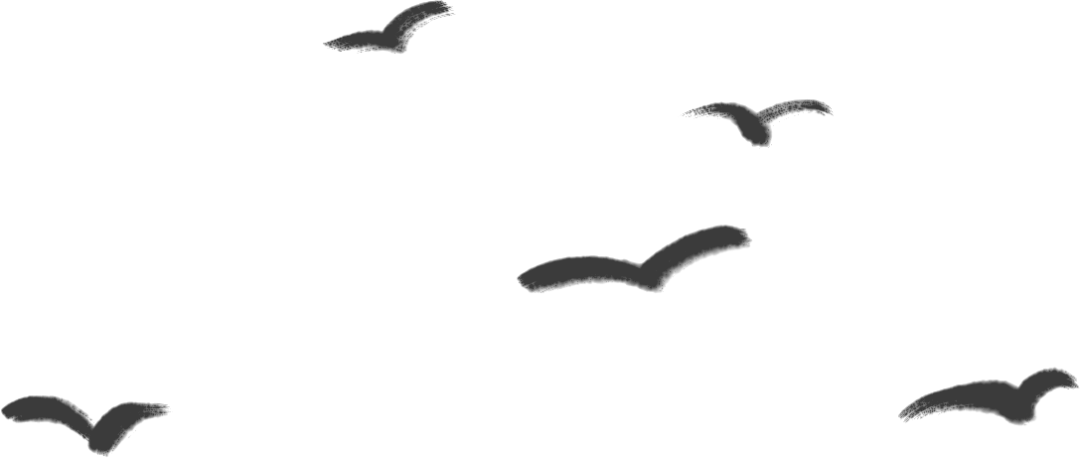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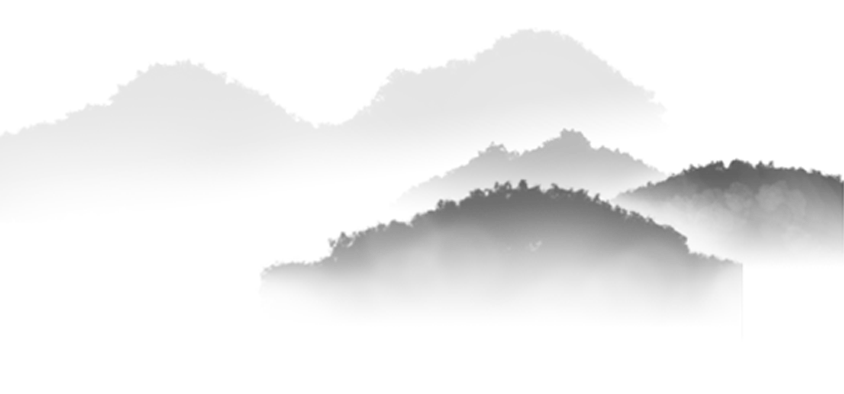

肖瑞峰,浙江工业大学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先后获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浙江省特级专家。学术兼职有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已出版《日本汉诗发展史》《晚唐政治与文学》《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刘禹锡诗论》《刘禹锡新论》等学术专著。近年从事文学创作,以笔名“晓风”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江南》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篇小说数十篇,多篇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已出版中篇小说集《弦歌》《儒风》《静水》(合为“大学三部曲”)、长篇小说《回归》《湖山之间》、非虚构文学《青葱岁月的苔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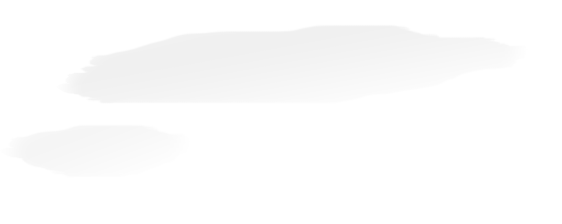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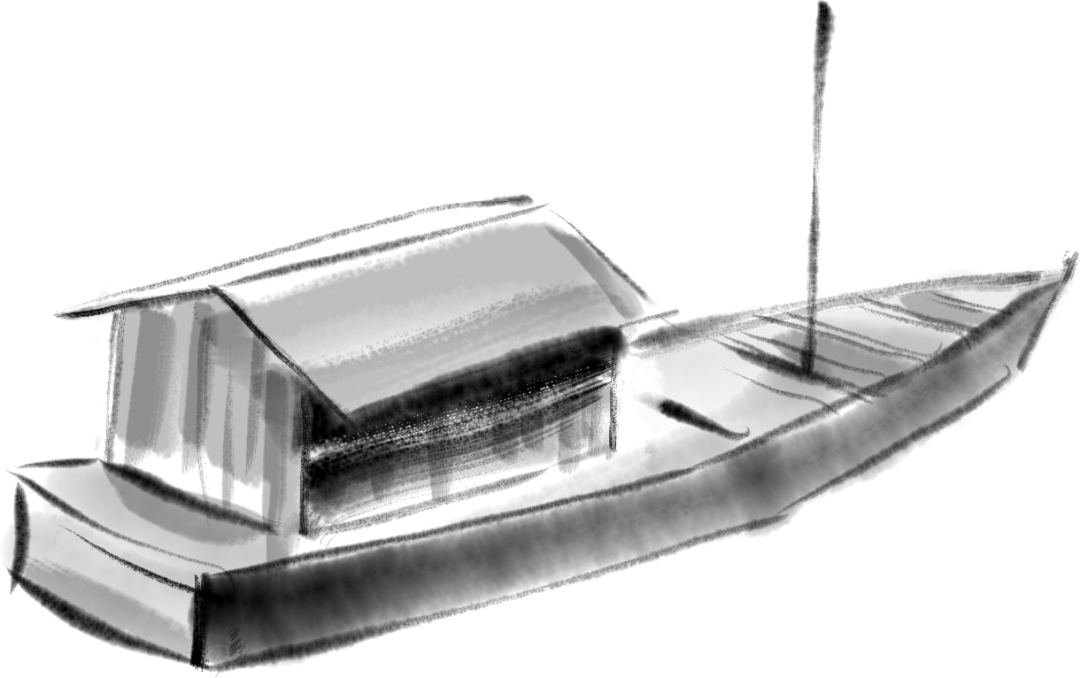
长摘要
唐诗新变视域中的刘禹锡唱和诗
对刘禹锡的唱和诗,学界早已有所关注。但对刘禹锡唱和诗的总体特色及其与“元和体变”的联系,无论是笔者还是学界同仁,都未及深究细辨,而这恰恰是研究唐代唱和诗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节点。元和是诗体大变的时代。审视元和诗坛接续开元诗坛之“再盛”局面,论者多着眼于其应对李杜登峰造极后的“新变”,并引用白居易“诗到元和体变新”的诗句以证成己说。其实,考察其前后语境,不难发现此句只不过是白居易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一诗中的“夫子自道”,贸然移用过来,作为对元和诗坛的整体认识,是有欠审慎的。但从另一视角看,既然这句诗恰好暗合了韩孟、元白、刘柳等元和诸公变革诗体的共同理念与实践,那么在明辨其原旨的前提下,借用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来评述元和诗坛的新气象、新风貌,倒也不能说是一种有意歪曲其本意的误用。
“刘白唱和”正是在元和前后诗体大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说“诗到元和体变新”这一自我总结客观上恰好可以作为元和前后诗坛风貌定评的话,这种求新求变的意向,从纵向的时间维度看,绵延于刘、白二人自元和年间崛起于诗坛始的创作全程(包括“元和”以后的“长庆”“宝历”“大和”“开成”“会昌”等“精华不衰”的时段);从横向的空间维度看,则贯穿于他们所涉猎的各种题材及体裁的创作全域。诚然,把刘禹锡诗置于唐诗新变的视域中加以观照,其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独标一格的的民歌体乐府诗创作以及对七言绝句等传统体式的提升与完善上,但即便仅仅从唱和诗这一并不特别亮眼的视点,也不难察见刘禹锡推进唐诗变革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刘禹锡唱和诗区别于同侪的特异之处非止一端,最令人叹赏的是渗透于其间的哲学元素和哲理意味。刘禹锡本来就兼有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多重身份,以哲学家发而为诗,不期然地映现出思想的光波和哲理的刻痕,即便是唱和诗也往往带有哲学思考的色彩。如《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作为一首奉和白居易的哀挽之作,诗人却没有沉溺于伤逝之情,在稍作叹惋后便笔锋一转,从新陈代谢的认知视角阐发了他对生死的独特看法:“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意谓人之生死轮回,一如新叶与陈叶的嬗替、前波与后波的更易,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宇宙万物因此才能循环无已、生生不息。结尾处暗寓顺应自然规律的流转而从容看待人间衰荣的倡议。正因为他能摆脱庸常、固化的思维模式,将个人生死放到大自然无限循环的寥廓视野中加以观照与评判,才能最大限度地稀释友人辞世给自己带来的心灵忧伤,表现出超拔于白居易原唱之作的高旷。而这又给他的唱和诗注入了哲思的元素而平添了为宋人导夫先路的理趣。
我们不敢说在唱和诗中寄寓哲理始于刘禹锡,却有理由说,有唐一代在唱和诗中较多地寄寓哲理,当首推刘禹锡。诚然,刘禹锡阐发哲理的作品并不限于唱和诗。他的咏物诗、咏史怀古诗及民歌体乐府诗也以融入哲理为能事。如《浪淘沙词九首》其八从自身对待贬谪的旷达态度入手,将大浪淘沙、真金不灭的朴素真理贯注在字里行间。因此,以哲理入诗可谓刘禹锡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唱和诗也不例外。事实上刘禹锡的唱和诗正是凭借哲理元素的浸润与渗透,在同侪中独标一格,呈现出新异的风貌。《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中国古代唱和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不只是因为对偶工整、语言精粹,更因为诗中虽不免自伤沉沦,却能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一己之困厄。其措笔之妙在于上下勾连、前后照应刘禹锡的诗全集,既顺势呼应了白居易对其坎坷遭际的叹惋与同情,又通过对升与沉、荣与枯等辩证关系的形象化解析,不动声色地展示了自己有别于白居易的达观情怀。
早在刘、白唱和之初,刘禹锡就已显露出喜作哲思、乐谈哲理的迹象。在两人晚年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时,以唱和诗体寄寓哲理,就成为刘禹锡更频繁的创作行为与更自觉的艺术追求了。“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这既是对自身历尽沧桑的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具有普泛意义的人生哲理的阐释,或者说从哲学层面对人生历练和生活感悟的提炼与升华。
从唐诗新变的视域考察刘禹锡的唱和诗,其另一卓异之处是豪健爽朗的抒情格调。他以衰迈之年奉和白居易的作品,不仅比原唱之作多一层哲学思考,而且表现出远胜于原唱之作的高旷胸襟和豪迈格调。如《酬乐天咏老见示》《乐天重寄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等篇,我们把它们孤立地看,或许还意识不到其卓荦不凡,但如果与原唱之作参读,就不可能对其胸襟之阔大、格调之高朗全然无感了。白居易《咏老赠梦得》一诗细致地描写了步入晚境后生理与心理的双重不适,流露出慵懒、衰颓的消极情绪。出于唱和应有的礼仪,刘禹锡的和诗虽不免在前六句违心地加以附和,后六句却一反其基调,倾吐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高亢心声,将其不服老迈、渴望有所作为的烈士情怀轩露无遗。
刘禹锡唱和诗的抒情格调当然是多元呈现、不拘一格的,但从总体上看却以豪健爽朗为基调,在因人、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奏中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底色。这一底色覆盖其唱和诗所涉猎的各类题材,而在奉和白居易的咏老之作中沉淀更深。“商山紫芝客刘禹锡的诗全集,应不向秋悲。”“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凡此,都体现了他一如既往的亢奋与昂扬。
其“新变”的另一侧面是对艺术形式的极致追求。正是凭借内容与形式的双轮驱动,刘禹锡才健步登临到唐代唱和诗的巅峰,从而成为有资格参与“华山论剑”的高手。最能映现其唱和诗艺术追求的是以下四点:
其一是体裁丰富多变,不专于唐代唱和诗习用的五七言近体。尽管其唱和诗中传诵最广、意蕴最深的作品几乎都是七言律绝,但他实际运用的体裁还有五七言排律以及六言、杂言、宝塔体等,可谓不拘一格,变化多端。无论试手何种体裁,无不得心应手、意到笔随,即便是难得涉笔的六言体和杂言体,也呈现出驾轻就熟的浑成气象。这充分显示了刘禹锡唱和诗在体裁运用方面的不主故常、富于变化。
其二是精华内敛、微言寄讽的独特笔法。刘禹锡唱和的对象是纷纭复杂的,这就决定了他的唱和诗除了运用多种体裁外,还必须区别形形色色的唱和对象,采用不同笔法。他与牛僧孺、元稹等人唱和时所采用的精华内敛、微言寄讽的笔法,既反映了士人普遍明哲保身、三缄其口的时代症候,也是步入晚境后的刘禹锡应对机弩四伏的政治环境和隐患丛生的文化生态的机智选择。而这又给唱和诗赋予了一种绵里藏针、神余言外的表达方式。
其三是典故与比喻的精当运用。刘禹锡写诗酷爱用典,乃至给人“掉书袋”之感,唱和诗尤其如此。偶有运用过度乃至失当的个案,但足以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更多的成功实例。诗人巧妙遣用典故入诗而能做到化合无痕的艺术功力,较之李、杜等“顶流”诗人亦未遑多让。而且,他常常将意蕴丰饶的典故和形神兼备的比喻叠加在一起,联翩而发。
其四是以戏谑笔调营造谐趣。戏谑或曰谐谑是宋诗的特点之一,但戏谑笔调在唐诗中早已显山露水,只不过气象未成、声势未壮。在唱和诗中出以戏谑之笔的唐代诗人不只是刘禹锡,但他所作却似乎最合乎戏谑定义,即诙谐幽默感更为显豁。如《答乐天戏赠》几乎通篇都是无伤大雅的戏谑之笔,既披露了诗人平日压抑在骨子里的俏皮,也显示了这两位形影不离的诗友彼此间可以放言无忌、恣意调侃的淳厚交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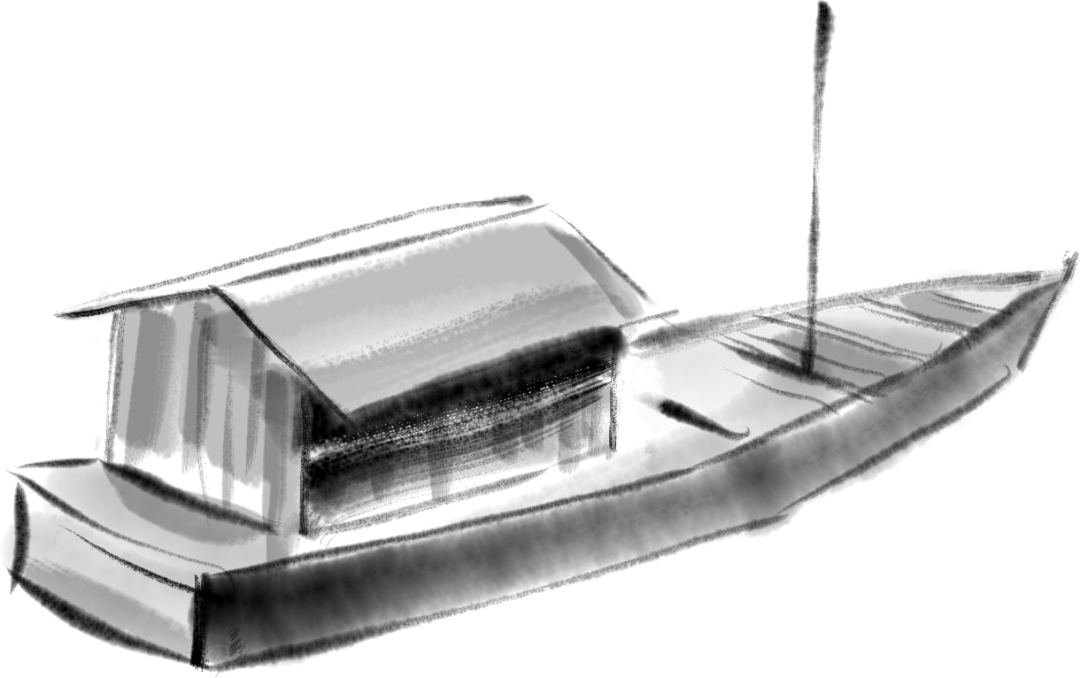
全文详见《文学遗产》2023年第5期
限时特惠:本站持续每日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课程,一年会员仅需要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长微信:Jiucx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