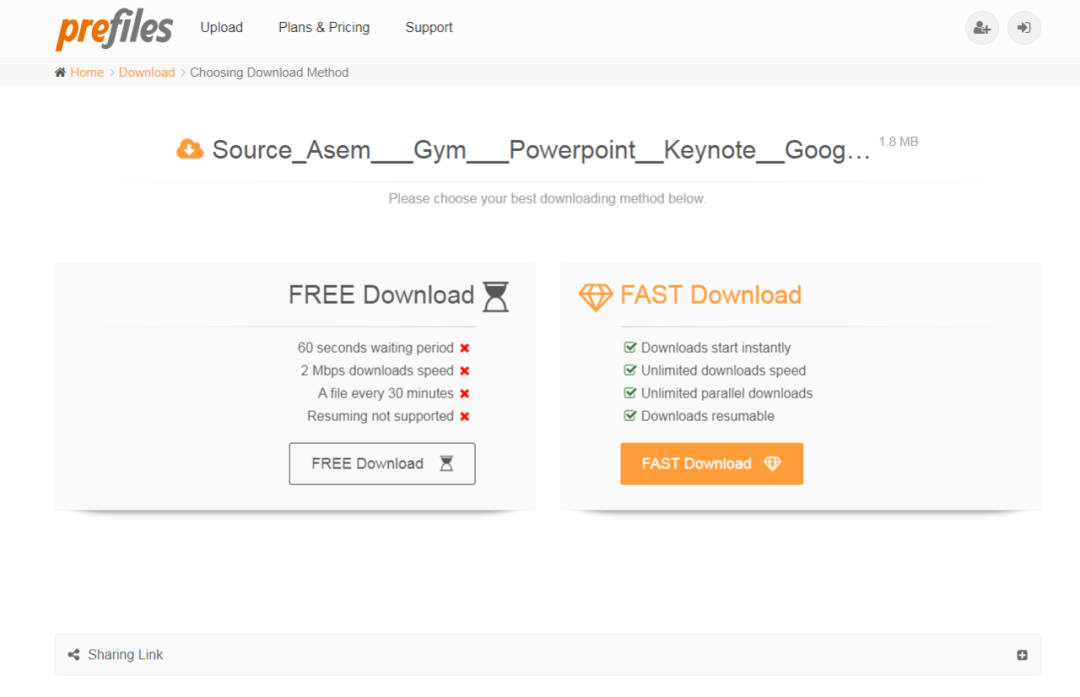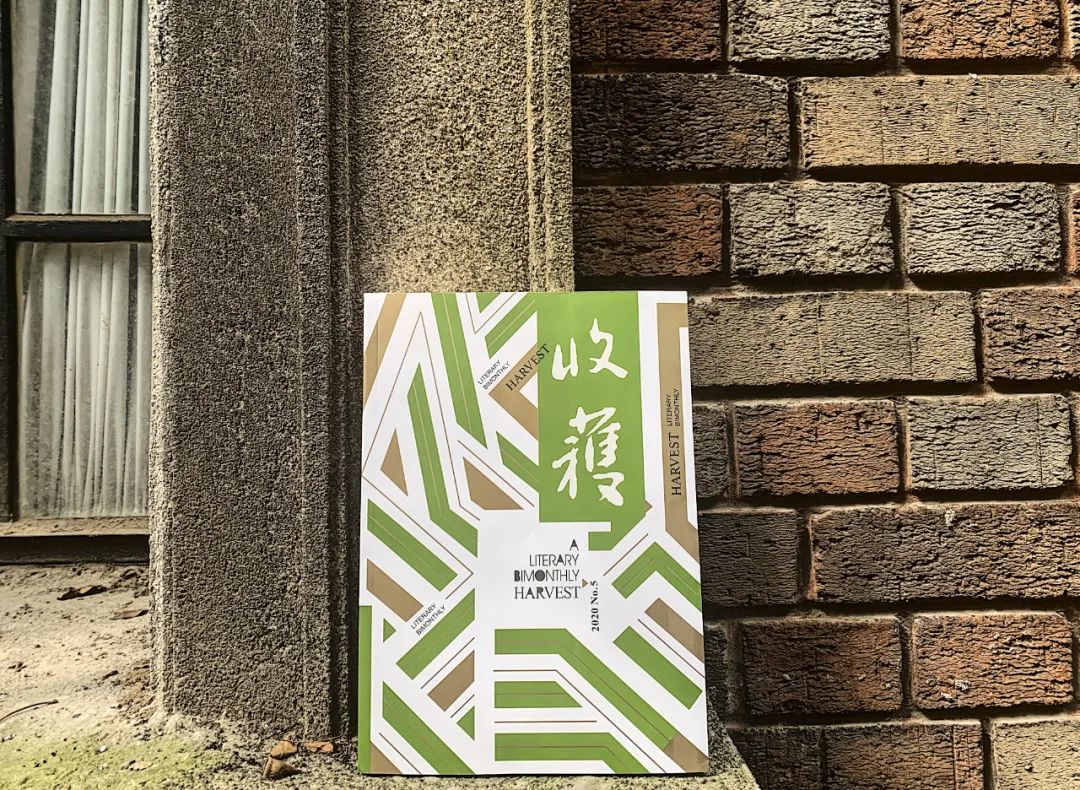

《女嗣》索耳(2020-5《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小说讲述的是一对互为镜像的表姐妹在粤西宗族社会的规则中挣扎生存的故事。“我”是一位曾经打遍街机无敌手的“男人婆”,爱谈男朋友却不结婚;表妹是一位脑洞异常的中学生,校园舞者,Vlog达人。两姐妹表面上关系冷淡,其实偷偷关注着彼此,直到有一天,表妹发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另有其人,决定离家出走,导致她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戏剧式的颠转......小说延续了作者一贯的文体创新意识,“不分段”和“逗号”的使用是小说的两个明显特征。作者有意采取这样的叙述方式,但并非为了形式而写作。整篇小说的叙事和情绪都呈现出自然连贯的状态,切换自如。
不能乘风破浪的姐姐
——读索耳《女嗣》
文 / 唐诗人
读索耳新作《女嗣》时,我刚看完芒果TV女团成长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最后的收官之作。一个热闹了几个月的综艺节目,最后的成团之夜特别喧哗。一大群“30+”的女艺人一边完成唱跳节目,一边期待着最终的成团名单,内心和外表都洋溢着热情。节目最后,一个又一个成团名字公布出来,伴随着的是欢呼与泪水,甚至还出现了张雨绮演讲式的“独立女性”成团感言。这些“姐姐”的声音持续作用于我已经转移为阅读《女嗣》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当然,导致我的心思无法从一个综艺节目中走出来的缘故,主要还是因为小说《女嗣》所讲述的故事也是围绕着女性而来的,与“乘风破浪的姐姐们”有着共同的话题。
“嗣”的意思是子孙后代,指向一个家族、家庭的继承人,“女嗣”也就是女继承人、女性后代。索耳的《女嗣》这个小说讲的就是女性后代之间的故事,其中的两个核心女性角色是表姊妹关系。女性叙述者“我”,在小说中是表姐,三十多岁,属于《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姐姐们的年龄范围。小说中“我”的表妹则是一个读初三的姑娘,是舅舅舅妈从儿童福利院里收养的女孩。《女嗣》的情节很简单,就是发生在“我”这个大龄未婚“浪姐”与表妹这个低龄任性“浪花小姐姐”之间的故事。
多少年了,女性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尤其三十以上的女性相关话题,更是屡屡引发全网、全社会讨论。2020年上半年,因为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以及都市情感电视剧《三十而已》的火爆,更是把大龄女性的生活、情感和工作等各方面问题推到了网络公共空间,各种各样的女性遭遇成为“热搜”事件,被大众吃瓜,被各类自媒体号点评议论。整个社会会有热情和兴趣持续不断地讨论大龄女性一类话题,这当然与大龄女性在这个时代曾经遭遇或者正在遭遇的各种难处直接相关。我们翻看微信、微博上相关文章或者话题所引发的网络点评,可以感受到很多观点、评论的背后,都是一些曾经有同样或类似遭遇、有共同感受的女性,包括很多男性,也愿意以一种或情绪化或理性化的方式对大龄女性的遭遇或言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全民共话的问题,或许也可以视作一个时代性的文化语境,起码它表征着这个时代的部分情绪。而索耳作为90后青年作家,作为即将进入“30+”人生阶段的男性,这种身份对于当前时代的女性问题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吗?以至于要以小说、文学的方式来表达。
《女嗣》故事看似简单,人物关系也不能再清晰了,但要真正理解这个小说并不容易。这种理解上的难度,并非叙事有多晦涩,而是主题本身的复杂。更准确地说,这种晦涩应该是来自于小说所呈现的这段生活事件。《女嗣》所展示的生活,有着太多的细节,包括物质细节和心理细节,都很丰富,而且细节之间充斥着左冲右突、矛盾诡异的特征,想确定作家的叙事意旨和文本的具体意蕴是有难度的。当然,这种难度在很多时候也可以理解成小说的张力,意味着这个文本敞开了足够多的可供思考的面向。比如我们可以从性别歧视问题进入其中,看到的或许就是作家要表达的传统家庭观念中的“女嗣”问题。“我”是独生女,但“我”父母却总是希望“我”是个男孩子,这种性别歧视导致“我”小时候特别叛逆,故意表现得“比男孩还男孩”,喜欢打架,被人喊作“男人婆”。因为父母、家庭的重男轻女心理,导致“我”变得男不男、女不女,慢慢成了人们眼中的怪胎,甚至于逆反到自我伤害、自我放纵。从这个角度来看,《女嗣》讲述的就是一个传统家庭在传宗接代问题上过分性别歧视导致了“女嗣”的叛逆成长和残酷人生,这可以视作《女嗣》这个小说的一种叙事意旨。但很明显,这一类想法太过平常了,无数乡土的、现代的小说都在阐述这样一类传统观念的“吃人”本质。而且,《女嗣》之所以写了父母、舅舅舅妈一辈人对待“我”这个反面教材式“女嗣”的态度,也是为了丰富“我”的形象。
小说中的“我”,并非简单的传统家庭重男轻女观念的受害者人设,“我”更是一个清醒的知道一切的成年女性。“我”在自己的世界里毫无追求地活着,“我”只追求身体自由,只是一个有身体欲望但没有生活希望的大龄女性。“我”很清楚亲戚们如何看看待“我”,“我”也刻意跟他们保持距离。亲戚们也排斥“我”,“我”是整个家族的另类。“我”不爱笑,不愿意与家族、家人保持一致的“微笑”,“也不好好读书,跟人鬼混,高中没毕业就跑去珠三角打工,二十年来没存什么钱,勾搭过很多男人,却没一个成事的对象,这年纪看着也快四十了,在我们这里,完全是失败的女性范本……”从家庭、亲戚的眼光来界定“我”的话,简直一无是处。但“我”需要为自己的人生、生命寻找和确认价值。“我”不断地找男人,放纵自己的身体需求。同时,“我”也慢慢发现了表妹与“我”年轻时打掉的孩子年龄相仿,为此想从表妹身上感受到新的生命希望。然而这一切对于“我”而言,都是虚妄。“我”找的男人全都是出现然后潇洒转身永远消失,而“我”寄予热情的表妹其实根本就不在乎“我”,她只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女孩,对于“我”的忧伤和喜悦都是无感的。
如果我们仅仅把《女嗣》理解成重男轻女、性别歧视一类问题,这可能是对作家叙事雄心的羞辱。小说中还有那么多细节,包括小说中差不多与“我”这个叙述者同等重要的表妹这个形象,它们的存在并不是工具、摆设,它们与“我”的成长遭遇、生活现状相比,一点也不次要,甚至更为核心。就如表妹这一形象,我们只有理解了表妹这个角色的意义,才能把握小说更为难得的精神内涵。
“我”想从表妹身上获得一种身体和精神的解脱感,然而表妹并不是“我”所能掌握的孩子,她的能力、心理世界以及价值认知、家庭观念等等,都不是“我”这个大龄表姐能够把握和理解的。在自己的一系列行动遭遇失败之后,“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无力:“我才感觉自己干净了,平静下来,这些日子来到底做了多么可笑的事情,哪怕你做得再可笑,也不能使这个环境更可笑一点,而你越想让它改变点什么,自己就变得越发可笑,无休止地可笑下去,在这个圆形、苍白的卵里,我按时吃饭,活动,睡眠,非常安全,不用担心在外头漂游时被人扔石头,不用担心各种陌生语言的侵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兄弟姐妹,每一份友爱里就含有一份毒素,我在这份友爱的保护之下,同时也生吞下这些毒素,并不是说没有意识到毒素的存在,而是它们让我感到安全,安全第一,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我”这个另类的表姐,想从几乎是下一辈的表妹那里获得一种新的生活热情,然而这个表妹回应“我”的,与“我”的其他亲戚所提供的并无差别。它们都是爱,更是毒素。“我”走不出亲戚包围的世界,意思是走不出自己的家族,摆脱不了自己身体里留着的血脉。因为血缘关系,家庭、家族禁锢着它的子孙后代,当然也禁锢着它的女嗣。“我”是这个家族的另类,要活得最真实,不想被这个充满着虚假微笑的家族所同化,最终也只能是从“另类”变成“败类”。
“我”终究只是自己,而且这个“自己”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自己”,也不是他人想要的女嗣,“我”只是一个被“圆形的、苍白的卵”所包裹着的另类、败类。即便“我”曾经叛逆、曾经逃离,最终也不得不回归到这个苍白的卵中,无声地忍受着那些无感的爱,被养育,也被慢慢毒死。“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嗣怎么读,这样的“我”,能乘风破浪吗?在索耳的小说世界里嗣怎么读,根本就没有什么乘风破浪,有的只是女性的负重前行,甚至说“前行”都显得矫情,只是活着而已。在“我”这里,感受到的只能是绝望。这份绝望,已彻底包裹着“我”。这种彻底,不仅仅是“我”无法摆脱自己的家族,不只是说“我”这个女嗣根除不了自己身上流着的冷漠的血脉,更令人绝望的事情其实表现在表妹身上。表妹这个与“我”的家族没有丁点血缘关系的多才多艺的女孩,却也与“我”的亲戚们有着同样的性格、形态与表情。
在性格上,表妹喜欢说大话、谎话。“矜贵,好笑,极自私,不可理解,满口谎言”,这些性格,连她的养父母,也就是我的舅舅舅妈都受不了。而“我”爸妈、舅舅舅妈本身就是最喜欢说谎话的一辈:“她爸妈已经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会车大炮的那一批了,对,舅父舅母,包括我父母,还有他们的同辈人,六七十年代的过来人,在无数的车大炮中存活下来,而我的舅父舅母还是其中最优秀的亲戚,仍然忍受不了她的谎话,每次聚会时,我们倒宁愿她是个哑巴,她也确实不爱搭理我们。任何人。只要一张口就是谎话。”“车大炮”就是谎话连篇,这是“我”父母一辈人的共性,起码是“我”父母、舅舅舅妈等这个家族的父辈共性,他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也继承着这样的品性。即便是没有血缘关系,也阻挡不了这种文化的遗传。还有身体特征,表妹这个跟“我”的家族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女孩,却有着“我”的家族的鼻子:“我都能第一眼认出这个鼻子,跟照镜子似的,我没法逃过这个群体幻术,里面的每个成员都无法逃脱,可是,面前这个稚气未脱的少女,跟我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不知道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我们父母经常这样骗自己的孩子,她为什么也有我们的鼻子,这等于说,我们的鼻子不受基因支配,而是文化所导致的。”连身体特征都可以跨越血缘地相像,这种家族文化对人的影响、塑造是有多深刻?表妹与“我”的家人们太像了,这种“相像”让我们痛恨她。“我”怂恿或者支持她离开舅舅舅妈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其实是希望她摆脱“我”的家族文化。表妹的逃离,对于“我”而言就是一种希望,“我”幻想着这个“女嗣”的出逃,再不回来。然而,现实是“我”逃不了,她也逃不了。“我”,或许还包括很多的家人,都“想把自己从人群里赶出去,扔出家族的门槛,却又一次次地,慢吞吞地爬回来,哪怕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哪怕是挣扎着,也要回到故土,没有这个宗族的文化黏液,我们无法赤裸着活下去,一代接着一代,越抱越紧,越恨越深,终于每个人都变成膨胀又空虚的泡沫”。文化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很多时候却表现为禁锢。这种影响、禁锢是超越血缘的,也并不局限在某几个家族。表妹离开“我”的家族,“她可能只是从一个坑里,跳进了另一个坑里”。
没有希望,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我们的过去。这“过去”包括作为生命根源的血脉,包括作为文明历史的文化习性,当然也包括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过去。小说中的“我”,逃离不了自己的家族,也忘不了自己的过去。家族亲戚们的习性,自己身体上、心灵上留下的疤痕,都在束缚着、禁锢着“我”。“我”年轻时候堕胎犯下的错,已经深深刻在了“我”的身体,无论它表现为痛楚,还是表现为欲望,都指向一个沉重:“如同悬挂着几十斤的铁球,把我直拉回地面,把我撕扯得剧痛,喘不过气来,那个孩子来报复了,我知道,不只有他,他还带来了他的兄弟姐妹,他们抱在一起,原来他们是这么重。”把“我”拉回地面的,是血脉、是文化,把“我”撕扯得剧痛的,是家族、是孩子,把“我”埋葬在耻辱里的,是记忆、是伤痕……这些力量根深蒂固,“我”一个小小女嗣又何以对抗?“我”,还有这个任性的表妹,几乎是两代女嗣了,终究都无法逃离。小说结尾,很早就被自己作为医生的同学诊断为再也不能怀孕的“我”,却意外地怀孕了。被朋友、专家的安全话语所环绕着,居然也会有意外。这个意外是希望吗?或许作家不忍心把小说写得太绝望了,特别给最后安排一个突如其来的孩子。可是,这个孩子太“突兀”了,它不会有父亲,也不会被“我”的家庭真正待见,如果是个女嗣,她能逃离“我”的命运吗?
没有乘风破浪,没有豪情壮志,当然也没有独立宣言。《女嗣》里的表姐妹,不是《乘风破浪里的姐姐》里的“小姐姐”,也不是《三十而已》里敢爱敢恨、能进能退的都市女性,后两者对于《女嗣》里的“表姐妹”而言,都太奢侈、太遥远了。理解了“女嗣”的深层次绝望,或许就能感受到索耳要通过《女嗣》来表达什么。作为作家,索耳以文学的方式抵抗着这个时代的时髦话语。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在舞台上光鲜亮丽地表演着个性和独立,然而在舞台之外呢?生活世界里的女性,她们能摆脱家庭么?能不被自己生活所在地的文化传统所塑造吗?她们又能够真正走出自己作为女性从小到大所遭受的那些伤痕记忆吗?
如果我们把《女嗣》这个故事不断放大,这个世界的女性,又有哪个逃离得了“我”或者“我”表妹的命运?像“我”这样的,曾经无比叛逆,但终究要回到那个充满爱和毒素的家庭,始终要作为某个家族的女嗣被强韧的文化习性所吸纳;又或者,像“我”那捡来的表妹那般,在网络上绽放着自己的才艺,通过表演获得满世界的爱,然而,她也不过是被意味着权力和资本的养父养母供养着,即便任性一回找到了自己的根,也会迅速逃回到权力和资本的温暖怀抱。作为“根”的东西总是原始的、粗粝的,它们不会被带到舞台上,不会被表演出来。新媒介时代,女性只会被要求穿上靓丽的衣裳,涂抹上最精致的妆容,然后去表演最梦幻的故事。但古老而严肃的文学不同,女性落入作家的笔端,往往是表现为赤裸裸的形象。索耳更进一步,他写《女嗣》,感觉是拿着显微镜看女性,他看到了她们的伤痕,看到了她们的欲望,也看到了她们的绝望。看到还不够,他拿她们做标本,解剖,发现“她”的背后还有很多“她们”。
本文作者简介:
唐诗人,暨南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收获》2020-5
《收获》微店


2019 收获文学排行榜
中篇小说榜(上下册)
短篇小说榜(单册)
来自店长
《收获》微店
限时特惠:本站持续每日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课程,一年会员仅需要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长微信:Jiuc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