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摆渡人生,回望尽泫然
——悼我的大姨父
阳春三月,赵国西南高原,蓝天白云苍狗,樱花妖妖娆娆如商业区靓女。我从A赶到B,然后从B赶到C,然后赶到D。我不日理万机,我要赶到D而已,赞美主,一路蹭车,脑子出轨安全容易。
姐来电话,云:大姨父去世了,她和弟弟去吊唁。
我的思想不敢在别处出轨,只静静地回忆着大姨父如摆渡船般的一生。
四、五岁时的记忆,大姨父是一个叫付家沟的地方生人,离我家二十多里地,你应该明白,于我而言,很是遥远,于今天而言,相当于乌鲁木齐,或者哈尔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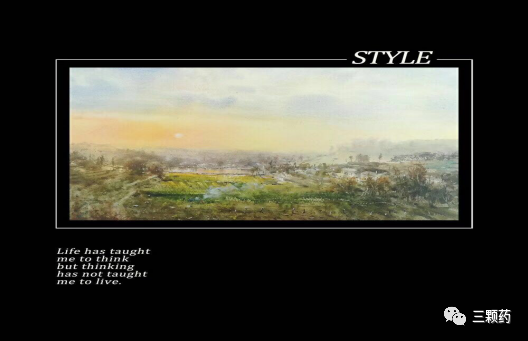
他是一个手艺不错的剃头师傅,他是一个高挑帅气的剃头匠,在栏江河畔的古场镇上开一店面,然后与我大姨成婚。大姨说:“我父亲去世早,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泫然是什么意思,母亲辛劳得厉害,你跟我回乡下,照顾这一家子?”剃头师傅回了一趟付家沟,回来说:“我已禀明父母兄嫂,他们同意我去你家里。”小夫妻回刘家湾,扶持刘姓一家子。
赵家为王,那时民生极其凋敝,饿死人数以千万计。小夫妻鼎力而为,让我外婆、母亲、小姨和两个舅舅活着活下去。大姨说:“母亲想让小弟成读书人。”大姨父说:“行!”当然就行了,他考上大学,后来成了工程师,然后是另外三个的成人、嫁、娶。这样说着如灯草般很轻巧,我老实告诉你或你们,除了阳光下土地上苦苦挣扎,免不了后半夜去生产队里偷东偷西,否则这家子也是要死人的。在那时的赵国乡村,不偷不摸能够活下去,我是不信。
关于这个不信,可以给个注脚。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仍然是赵家秉持国政。一天,晚饭已吃了一大会儿,大舅家的表姐表弟背上背篓,暗示我一道出门。出了竹林,上土阶数十百步,穿过大姨父家的房屋,到了他家屋后的一遍地里。哇,二、三十条人影在麦地窜。我明白,他们在偷队里的将熟的麦穗。那是五月初,人们都饥饿得眼放绿光,只偷麦穗,回家手搓棒捶,能解燃眉。第二日我故意溜达到那片麦地旁,大姨父也在,望着踩踏得稀里哗啦的金黄色麦秸。我欲言又止,他用手指搭嘴示意。他是这里的小队长,管理着刘、秦、张、罗、兰五姓的百十号人。我那时是红小兵,少年刘文学的故事也熟识于心。英雄的壮举总是伴随着死人,小队长大姨父不是英雄,少年如我也不是。偷来的粮做成食,感觉比平时的饭食香喷很多。为什么?科普一下是什么意思和道理。其实,偷还是非偷,这是一个问题。脚踩着赵,还是非赵,结论自然不一样,饥饿的人要渡河,哪个来摇船摆渡我?人性的光辉偷偷地照耀这土地,引领着大姨父这样的人们,静默中抗拒或抵消着高扬的阶级觉悟、革命情操及其风暴,将一些人摇摆到彼岸,避过饥饿、斗争、死亡的逼迫、追索。

还是回放到四、五岁,那里有我对于外婆和大姨父家最早的记忆。一间土坯茅草堂屋里,我坐在阔而高的理发椅上,我母亲坐在大姨的病床边,姐妹相对哀戚。大姨父从屋外进来,静立一旁。大姨努力地抬起眼,轻声说:“照顾好儿女,照顾好我的家人。还有,这房屋太破旧了,漏雨。”大姨父说:“你放心。”
第二日,大姨去世,一口薄棺材,埋在山坳里。
绳索密缠紧勒,人活得本已艰难,况且没了贤惠的女主人,况且茅草屋换成了石板瓦屋顶。表姐表哥表弟在贫困中生长,书没读下去,勤劳的品质却能完备。担心续弦孩子们吃亏,大姨父拒辞了几宗说媒。那时我常去外婆家,人很淘气,大姨父从未厌嫌我。每到春节,五分或一毛的压岁钱,也从未断过。
如若把所有的贱民饿死,赵家的未来是可以预见的,所谓万岁,只是个廉价的玩笑而已。所以在经历过一个漫长且比暴秦更过之的时代后,赵家要试着给人松一会儿绳子了。
那时我十三、四岁,开始读初中,然后去城里读高中,小姑、大姐、妹妹和小弟也未成年,个个都在上学。我家主要劳动力是母亲,父亲教学之外也干点农活。家里十来个人的承包地和自留地,总共十多亩,累死也闲不下来。
大姨父叫上大舅,招集两家的表兄弟表姊妹说:“你们二孃家的孩子还小,都还在读书,你们大孃去世时说亲戚要互相照顾。”从此,每遇我家忙不过,大姨父就带领七、八、九、十号人去帮助,我家的庄稼,比他们自己的还生长得好。我姐、我弟读到高中,我和妹妹都去上了大学,然后四人先后在城里立住脚跟,母亲也被接进城里,不再劳累。如若没有大姨父为主心骨的扶助、摆渡,我们的日子应该是另外的样子。
我们一家人都记得大姨父对我们的好,偶尔捎带点小钱给他,他却一个劲的说我们的好。大姨父啊,你才是真的好!

自从进入社会,我忙于教书,忙于坐牢,忙于牢狱后的重建家园,再后来忙于去工地打工,几乎再没去过外婆家那一方。今年1月底回家过春节,大舅家的表弟的儿子结婚,我和阿珍、儿子和弟弟、妹妹三家立马赶过去。二十多年未见面,我几乎还记得这村庄四十岁以上所有人的姓名,一一寒暄,他们很惊喜,说我没忘本。但我只知道,这里有我的根和本,我是从这里出发泫然是什么意思,被他们中的人摆渡到别的地方去。
大姨父家的两个儿子都有出息,或者在成都或者西安立足立业,让我欣慰。我在人丛中寻找大姨父的身影,人说他身体不好,不方便过来。我甩下众人,沿着熟悉的道路往后院奔去。阿珍、儿子、表姐、表哥和我弟、我妹跟着追过来。

大姨父披着厚棉祆坐在门口,听见我大声喊叫,颤萎萎站起来,腿脚弯曲着,手抖动着,努力着要辨识人。我大声地说出我的乳名,我大声说我看他来了,他才明白过来,不停地说好。大姨父老了,老得干瘪瘦弱了,老得猥猥琐琐,老得口水鼻涕眼粪都收拾不好了……我抓紧他的手摇,我的心紧缩疼痛,不忍久视。我的高挑帅气的大姨父哪里去了?我那能为一家、一小队百十号人抵挡赵家风雨风险的大姨父哪里去了?我不能忍受,往他口袋里塞下点什么,落荒而逃。
开筵席了,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情绪调整起来。觥筹交错间,我逮着同一外公家(我外婆为续弦)的大表哥喝酒,大集体大锅饭时期,他是这村上的队长,我大姨父的直接领导。我大声说:“大表哥,我要向你举报,今天席上,这个小队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是贼。三十多年前,有一天晚上,他们把大姨父家后面地里的麦子偷光了。我举报,身为小队长,我大姨父知情不报,纵容他们危害集体财产……”举座喧哗泫然。
宴罢,我带着阿珍、儿子去给外婆、大姨、大舅烧祭上坟。小舅似乎不高兴,想阻止我。我知道,在他的意识里,他上过大学,做过工程师,他理应相信共产党的所谓唯物主义的科学,所谓人死如灯灭,所谓烧钱化纸皆是落后、愚昧、封建及迷信。我是天主教教徒,原本不要烧钱化纸,原本不下跪于神、于主以外,但此刻,我长跪于坟茔前。”外婆、大姨、大舅,我来看你们了,是你们种的粮食、你们的话语、你们讲的故事送我到我喜爱的世界。”
车在高原之上飞驰,姐再次打来电话。“我准备了很多白布,垫在他的棺材里面。”我说,好好好好好好。
我闭着眼,心里七七八八,我在心底说:“大姨父,从此,你在彼岸,我们在此岸。可是,你能从我们这一辈人手里带走的仅此棺、白布。”
限时特惠:本站持续每日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课程,一年会员仅需要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长微信:Jiucx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