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论语》,可说是关于君子“修养以安百姓”的书。对内是如何修养君子,对外是君子如何安天下,即是常说的“内圣外王”。
关于修养的内容,据我统计,在《论语》484章节(依杨伯峻《论语译注》划分)中,直接涉及修养内容的就达102章节。可见,修养重要,而修德居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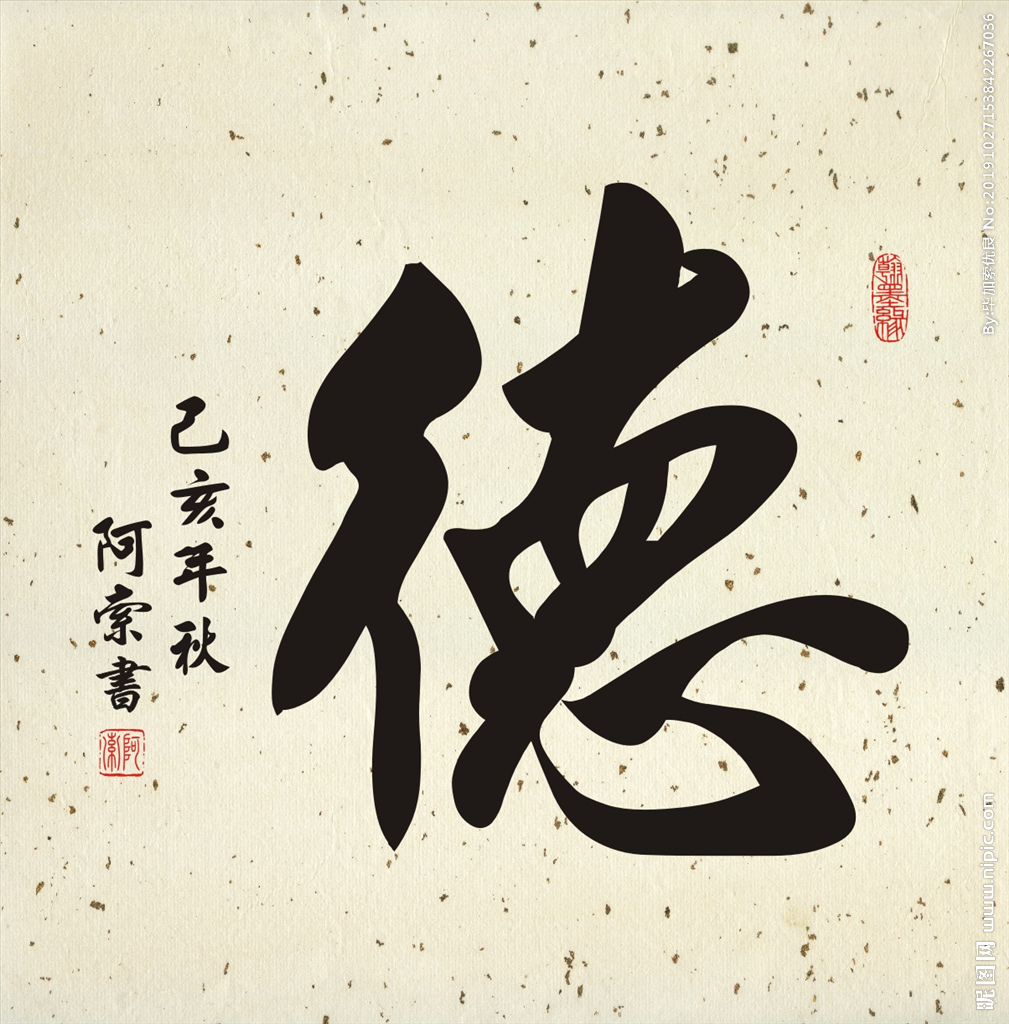
从孔子那时的世情看,人们对德的认识还处于不自觉、认识模糊的阶段。
孔子由此入手,强调要先“知德”: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论语·卫灵公》)
孔子之叹,是叹在世人知德太少,更叹在知德的意义非同寻常。当时人们尚未从"神性"转变到"德性"上,对德的体认远远不够。这里对子路说,更是教导弟子、指导人们,要高度重视德的问题,即“知德”。
孔子优秀弟子子夏,他所说的德,或者因为语境不可知,或者因为认识模糊: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
从字面看,子夏说大德要守得住、不出“底线”,小德可以“放点水”,这个理儿凭空而出,确实有些问题。
所以,后世朱熹等人批评为不够确切。对此,我们可以先设一问:子夏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这句话?如果这话是说在用于评价别人或大德小德形成对立选择时,这话是太正确了;如果说在普遍的修养问题特别是个人的修养上,这话就大错特错了。
比如,对管仲评价,尽管他不节俭也不够守礼、不守小信,但孔子格外推崇他“一匡天下”的“大德”,称之为仁,而子路、子贡却有过对管仲“非仁者与”的疑问(见《论语·宪问》)。这说明孔子在对待和评价别人时坚持看大节、看主流而不求全责备,大概就是子夏所说的“大德”;对自我修养,孔子等人一贯主张“责己以严”,对自己不能有半点“放水”。
对修养君子来讲,即使在日常言谈举止等“小德”上也要恭谨不放松,在特殊的时候即当在“大德”与“小德”之间作抉择或者在对人评价的时候,当然要以“大德”为重,“小德”要服从于“大德”,这才是孔子对“德”的界定,或者说是修己德、论人德的大纲。
从子路、子贡对管仲的“仁”的疑问来看,说明孔子弟子中在一个时期对“大德、小德”或“大节、小节”问题,在认识上是不到位、不统一的,他们还没有真正“知德”。至于子夏这段话德,是语境未交代而形成的模糊,还是子夏本身认识模糊,就不得而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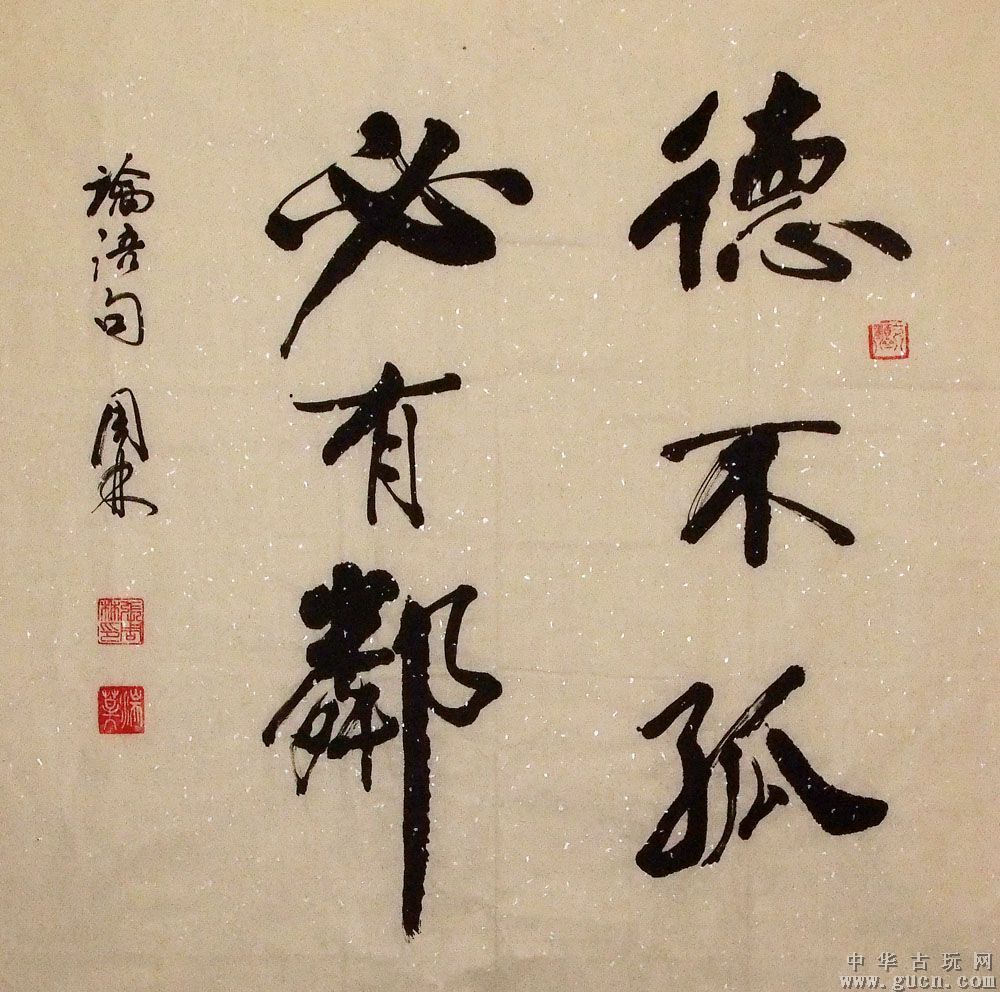
孔子明确指出,德的实质是内外善美的相辅相成。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先看通常解读:有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有邻居般的伙伴。
我始终怀疑这种解读,因为孔子自己有德但很孤单,所以才有“知我者其唯天乎”的感叹,哪有“邻”呢?所以他要造木筏漂到海外、要到九夷去寻找出路,他的“邻”又在哪儿?
再说那屈原品行高洁,最终自投汩罗江,他的“邻”竟在这江中;历史上有德而寂寞的人何能尽数?因此德,“德不孤,必有邻”,不是说有德就不会孤单,就必定有伙伴,而是讲德的特性、德的实质:德与人的内心有关(相邻),与人的外在有关(相邻),而与伙伴无关。
与孔子时代最接近、并且与孔子有渊源的《周易》中《坤文言》出现的“德不孤”,可以说明这一点。《坤文言》在对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的阐发中有“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
说君子用敬来规正他的内心,用义来规范他的外在(言行),有了这内心的敬和外在的义,他的德就成了一个具体的实在,而不是孤立的东西。由此看来,孔子“德不孤,必有邻”与此处是一脉相承。
在孔子看来,德不是一个空洞的、独立存在的符号概念,而是一个能够描述、能够看得见、能够体会得到的实际,它与内心良好的修养与外在良好的言行紧密相联、紧密相伴(邻),德不能脱离这内外之善而孤立存在,必定与之相邻、相伴、相表现。显然,在孔子的思想中,认为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知德”,也就不能很好地修德,这也许是孔子“正名”思想的具体反映。
朋友,我是清如静如,诚意与您一起对坐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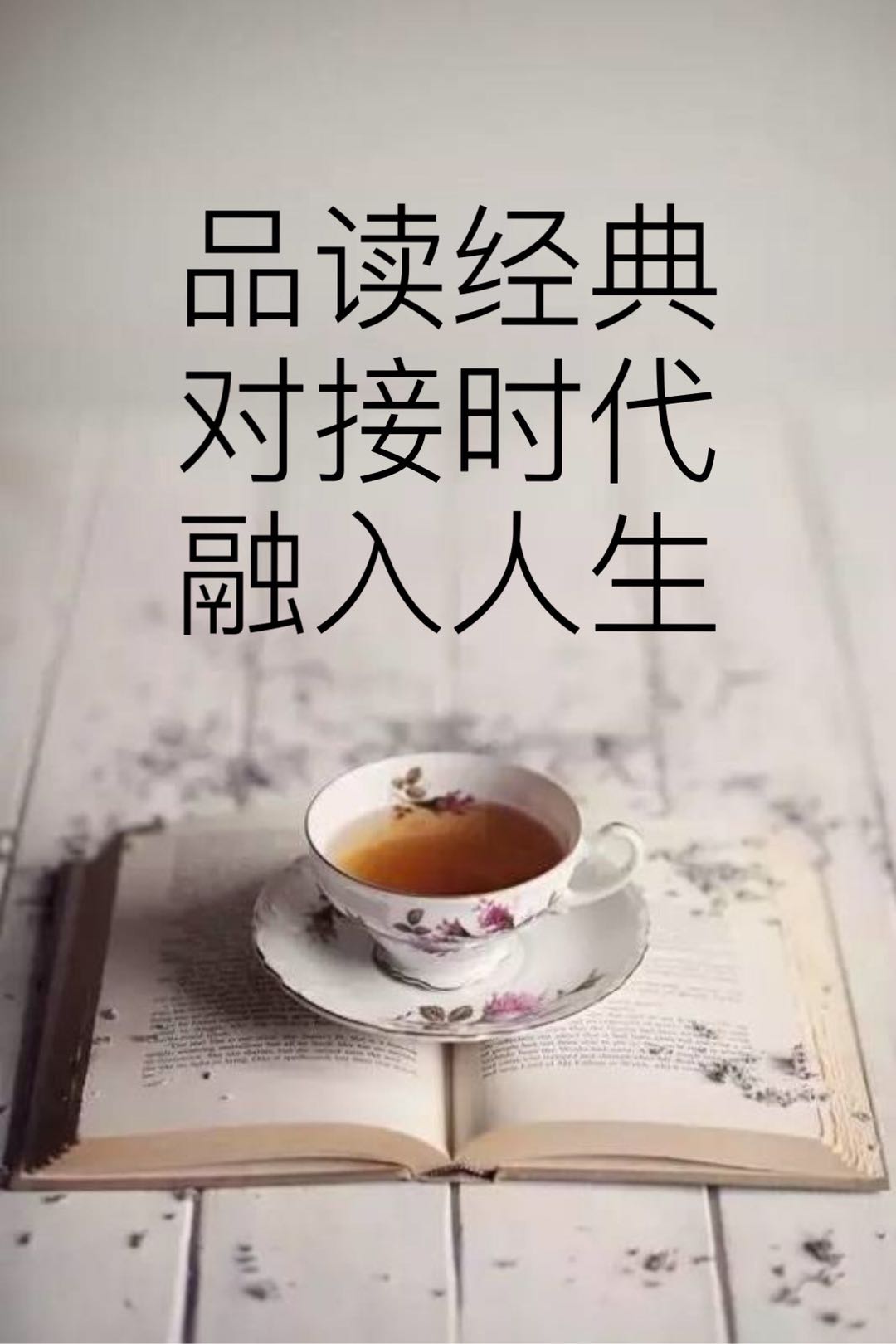
限时特惠:本站持续每日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课程,一年会员仅需要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长微信:Jiucxh



